

邺架轩读书沙龙第26期
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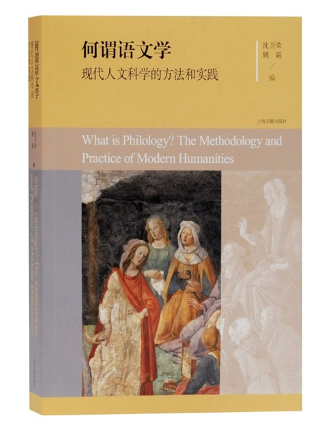
沙龙时间:2021年9月29日(周三)19:00-21:00
沙龙地点: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
主 持 人:王 巍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
主讲嘉宾:沈卫荣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系主任
姚 霜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水木学者”博士后研究员
主 办 方: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协 办 方:清华大学图书馆、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
直播平台:学堂在线、光明网


学堂在线直播二维码 光明网直播二维码
主持人:各位来宾,老师、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王巍,非常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晚上的邺架轩读书沙龙第26期活动,本期活动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沈卫荣教授,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姚霜博士来做这次的分享。沈卫荣教授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他的本科和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在德国波恩大学获得中亚语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语文和佛教语文学研究。他也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专业学科带头人。姚霜博士先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后来在清华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她也是非常的国际化,现在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本次沙龙是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清华大学图书馆、邺架轩阅读体验书店、清华学堂在线、上海古籍出版社、光明网共同主办,在此也特别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光明网与清华校内各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因为不在北京,他们专程委托了沈卫荣教授向清华大学赠送本次活动的著作《何谓语文学》。接受赠书的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女士。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给本次沙龙的主讲嘉宾沈卫荣教授和姚霜博士,大家欢迎!
沈卫荣:谢谢王巍教授。在开讲之前我们先来看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小兵张嘎》中的一段,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其中有什么语文学的奥妙在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我提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语文学的经典案例?这个电影太老了,估计我们这里只有我比它老,其他人都比它年轻。这是1963年拍的电影,为什么我对这段记忆特别深呢?因为我小时候经常看它,记得当时我有一位好朋友长得跟这位翻译官很像,所以经常受到隔壁班同学们的嘲弄、嘲笑,有次他拉着我去跟人家吵架,就因为人家嘲笑他说“老子下馆子都不掏钱,别说吃你这几个烂西瓜?”最近有人把这一个段落放到微信朋友圈,里面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后来这个电影又被翻拍了,这个经典段子不断地在重演,这里面有句经典的话就是“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掏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在那个片段里面看到,他其实并没有说“老子进城里下馆子都不掏钱”,他说的是“老子进城下馆子都不问价,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大家想想,说“下馆子不问价”和“下馆子不掏钱”是两个概念。前面说“老子下馆子都不问价”,说明他很有钱,财富自由了,下馆子可以不问价,我有的是钱,我吃你个烂西瓜凭什么还要问价,这表明他是一个土豪,这样的话,其实八路军战士没必要和他去当真,碰到个土豪不挺好,本来10块钱一个瓜,现在20块钱卖给他,反正他有的是钱。但如果说他说的是“老子进城下馆子都不花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那就是恶霸了,想吃霸王餐,这样就可以跟他掏枪了。若从语文学的角度来讲,这二个句子完全是不同的台词,反映的完全是两个场景,反映出的是翻译官的两个不同的人品。这个电影后来的拍摄都变成是“老子进城下馆子都不掏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小时候隔壁的同学欺负我的好朋友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近来才知道原来并不是这样说的,翻译官或许并没这么坏,他就是炫耀自己是土豪而已,他并不是一个恶霸。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语文学无处不在。凡是有语言的,有言语的,有文本的,对任何一段话或者一段文字的解读、理解,实际上都是需要语文学在场的,不然的话,同样一段话的理解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引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什么是语文学?今天我们两个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语文学,然后请姚霜博士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本书,即《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到底是怎么成书的?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
今天到场的朋友中可能有些人听说过,但大部分人可能连“语文学”这个名称都没听说过。很多年前我开始谈语文学的时候,人家问我你是不是讲小学语文、中学语文或者大学语文?我说对啊,跟这有点关系,但又不完全是。今天很少人会知道语文学跟现代人文科学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大概从调入清华开始,或者稍早一点,就开始在国内各种场合讲语文学。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依然不知道大家到底真的理解了语文学没有。我曾经在一篇文章说过,语文学是说不尽的一个话题。我希望这本书出来以后,大家能好好地阅读这本书,然后就能够知道什么是语文学了。我自己还是不厌其烦的来宣传语文学,倡导语文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俩都不是广义的语文学家,我们是做西藏学研究的,是做藏传佛教研究的专家。为什么我对语文学如此津津乐道,如此不知疲倦地讲语文学呢?这是因为我觉得语文学太重要了。所以,我今天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老调重弹,再谈一下语文学,我希望今天你们听完我们的报告后就知道什么是语文学了。
我还是从我个人对语文学了解、学习的经历来告诉大家什么是语文学。我最早是在南京大学学蒙元史的,就是蒙古史、元史。大家肯定都曾听说过一个人叫伯希和的法国人,他在中国鼎鼎大名。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给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世界汉学家谁是第一?可能说谁是第一人大家都会说“不,还有人更好。”但是你若说伯希和是世界上到现在为止最好的汉学家,大概没人会说不。就像我们现在说,陈寅恪是现代中国最好的学者,或有人会说王国维更好;若有人说王国维最好,也会有人说不一定啊,以前不还有钱大昕吗?但如果说是伯希和,那肯定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人说伯希和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把中国的古籍都能看懂的人。为什么?钱大昕难道不如伯希和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确实不如,因为在汉文古籍里面,其实不只是汉语,里面有很多是非汉语文的因素,它们可能有匈奴语、可能有突厥语、可能有西藏语、有蒙古语,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还有鲜卑等。纯粹的汉语文学家,就像钱大昕,可能是其中最厉害了,或可以把汉语文都看懂,但是凡其中出现了非汉语的这些词汇,他就看不懂了。如果在汉代汉文文献里面出现了一个梵文的字,音译过来的,或者一个匈奴语的字,一个突厥语的字,那么纯粹的汉学家是看不懂的。但伯希和除了懂汉语文以外,他还懂得很多很多种西域(中亚)的古代语文,所以他看到这些非汉语文的词汇,他又懂历史语言学这一套技巧,所以他就知道这个字、词在汉代的时候应该发什么音,这个字可以还原成突厥语的某个字或者还原成梵文的某个字,或者还原成古藏文的某个字,他都能读得懂。所以,到今天为止,就像乔丹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篮球运动员一样,我们说伯希和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汉学家。我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学习蒙元史,而伯希和做了很多蒙元史的研究,所以,我们当时都以为伯希和这套学问就是语文学,实际上更确切地说,他是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的专家,他把汉学和中亚语文学结合起来做汉学研究。
后来,我自己又从蒙元史转到另外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就是印藏佛教研究(Indo-Tibetan Buddhism)。这又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高级和精致的语文学研究,比如说你发现一个梵文的文本,你要给它做一个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就必须先要学梵文、藏文,给这个文本做非常细致的整理,把文本隶定,最后你给它做翻译,做注释。中国学者老说季羡林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学家,有西方印度学家说怎么没看出来呢?他可没做过一个梵文文本的精校本啊。印藏佛学是世界上又一个语文学的特别高精尖、高大上的学科,很长时间内我就以为语文学就是这样像印藏佛学这样的一门学问。
我自己一直努力在做一个好的语文学家。但是,这套学问确实太高精尖,太科学,某种程度上也太技术,做好太不容易了。也有人不服伯希和,他们觉得伯希和这套学问虽然厉害,可是伯希和都没写过任何一部通史性的著作,没有写过一篇有思想性的,很人文的著作。他写的都是一些注释和札记性的作品,例如他写的《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他写了好几本书,都是帮人家的书做注释;他读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给它做注解,结果自己也写成了一本大书。他自己从没写过一本通史,所以你怎么说他的学问好呢?一般人一方面喜欢神话化像伯希和这样的语文学大师,比如说我们说陈寅恪为什么厉害?因为陈寅恪懂很多很多种语言。为什么季羡林先生厉害?他懂很多种语言,觉得懂很多语言这个人就很厉害。但另一方面,你们这些人太厉害了,懂那么多语言,而我们根本学不了,我知道你厉害,但是“臣妾做不到”,没办法来跟你一样做语文学,于是就觉得你这套学问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太技术了,没有思想的火花,没有灵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的心在哪里?”因为我在德国时是做语文学学问的,我的博士论文在德国出版了,后来有位也算是当时我的博士生考试委员会当中的一个老师,就是现在在中国很有名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他为我的论文写了一个书评,他说这本书写的很好,按照我们德国的标准一定给它打最高分,书印得很好,语法都很正确,德语写得不错,可以流传一段时间,但他最后说我要问一句,作者的心在哪里呢?他觉得我们语文学家都是没有心的,而现在的学术都是应该有很多理论的,要有很多思想的火花,给人启发。他们认为语文学家做的语文学研究都是早就过时了的学问。对此我当然完全不认同。我从来认为自己是个语文学家,而且一直把伯希和这一套学问,把印藏佛学这一套学问,都作为最典型的语文学学术。常常用这套语文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别人的学术。
这里我们遇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好像这套语文学的学问早已经死掉了,现在只有少部分的人还在做这个学问,好像其他人做的人文学术都跟语文学没有关系了。这样的想法当然是不对的。我自己是学历史出身的,后来研究佛学,再后来我慢慢又从历史学更多转入语文学,以至来到了清华中文系工作。我觉得语文学这门学问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做的这些研究都可以算是语文学的研究。我刚开始想,我这是不是在不断地妥协,即不断地降低语文学的要求,我们不再追求像伯希和这样好的学问,甚至我们也不再追求像陈寅恪这样的学问,我们把语文学扩大化了,放低标准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很多的学科,不管是研究哲学、研究历史,还是研究文学,我们好像都在谈学科的危机,文学什么都研究就不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的人很多不满足于做一位哲学的解释学家,而坚持要做哲学家,可很多人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很多人研究德国哲学,包括研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但他们根本不懂德语。我自己在德国读书多年,但不要说看懂海德格尔,就是看懂韦伯就很难了,韦伯最容易的一本书可能是《儒教与道教》,但对我来说也不容易看懂,我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把它翻译成汉文的。我想如果一个人完全不懂德语的话,他怎么能去研究德国哲学、德国思想?研究历史的学者就更加困难了。我们老在说历史研究一直处在危机之中,自从我进入大学本科学历史,历史系的老师们一直在谈历史学的危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危机呢?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们缺失语文学的训练,或者说语文学已被彻底遗忘了,这导致了我们这些学科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学术了。所以,后来慢慢的我开始重新考虑到底什么是语文学?除了刚才说的像伯希和所做的这一套学问,像研究印藏佛教佛学的那套学问,是不是语文学与其他的学科也是有关系的?后来,从2016年开始我到清华开一门课,就叫《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就是要讨论到底什么是语文学?在很长的过程中,我慢慢地对语文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想法,从刚开始我觉得我是在妥协,是把语文学的标准不断地降低,认为如果大家都必须像伯希和这样做学问的话,那就没人敢做语文学了。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都很崇拜伯希和,但尽管崇拜他,很多人却不知道伯希和是做什么学问的。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反对伯希和,他们曾经有个说法叫Anti-Pelliot dogma,反伯希和教条,特别是英国的学者,因为他们做不到伯希和这种高精尖的学问,所以他们就讨厌你做这种学问。伯希和最喜欢写书评,做的二流的学问,他根本没法容忍,所以很多批评很尖锐,所以,不少西方人讨厌他,说我们不要伯希和那套学问。特别是到后来,整个汉学研究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China Studies,成为一个区域研究。它完全脱离了原来的语文学学科,变成了一个重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的学科,变成一个重现实研究的学科,把老的一套汉学方法,把伯希和的这套学问完全抛弃了。这就导致了整个学术标准的降低。
后来,我慢慢觉得,语文学应该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范畴(category),我总结我对语文学的理解,指出语文学应当有六个不同的范畴。其中,第一个范畴,就是它的本来意义,什么是语文学?语文学就是对言语、对文本的热爱,是love of words and text,这是牛津英语辞典给出的定义和解读。Philo-是爱,这个-logy就是言语,正好它是跟philosophy相对的,philosophy是对智慧的热爱。所以,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两种学问,一种是语文学,另一种就是哲学。哲学是你热爱思想、智慧,所以你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除了哲学,其他的一切学问都是对文本、对语言的爱,它们是学问,是语文学。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文知识,就是语文学和哲学两种。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们讲语文学,讲philology,就是指这个。
第二个层面,一切古典学术,从《荷马史诗》开始,到现代人文科学建立以前的这套学问,全都是语文学。现在中国讲古典学的可能不怎么重视讲《荷马史诗》,实际上西方古典学最重要的是两个阶段,一个是希腊阶段,重点是对《荷马史诗》的整理和研究,从亚历山大东征开始在东非建了很多的亚历山大城,各个城都建立了museum,就是图书馆和博物馆,他们就开始整理、收集《荷马史诗》各种各样的版本,发展出了一套后来成为语文学的最基本的学术方法,即把各种各样的抄本收集起来,开始建目录、建索引,编Critical Edition,就是精校本,最后给它做翻译和注释,做这样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罗马时代对拉丁文经典、对《圣经》的研究。古典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这套学问,这套古典学学术,实际上都是语文学。今天很多西方的大学,开始要把古典学废掉,说不应该叫古典学,因为古典学这个名称太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了,为什么希腊、罗马研究就是古典学,为什么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就不是古典学了呢,就不是classical studies了呢?所以他们现在要把这个学科去掉,直接改成希腊研究院、罗马研究院或者是中国古典研究院等等。就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后来改名为中国古典学院,我觉得这非常好,对古典文化的语文学研究都是古典学,这套学问整个是以语文学研究为基础的。有时候当我读们这一代学者所做的学术著作时会觉得很惭愧,觉得我们中国今天的人文学术,从学术标准来讲,甚至还达不到当时亚历山大城所做的学术,他们当时怎么写书、怎么做索引、怎么做脚注,可我们今天依然不会。以前常有人揭露很多博士论文甚至连个一个脚注都没有,这当然是不学术的。所以,古典学全是语文学,这是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现代人文科学就是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本来是不分文史哲的,它们都必须是一个语文学的研究和历史学的研究。为什么傅斯年先生要在中央研究院建立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所,把它定名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不是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所,而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是历史和语文学研究所。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首先必须是一种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它必须是一种历史学和语文学的研究。只有这样,它才是科学的、才是理性的研究。所以在现代人文科学这个范畴底下,就是研究宗教的、研究神学的、研究哲学的,他们都必须是一个语文学家,都必须是一个历史学家。神学教授们也都必须是语文学家。实际上现代人文科学的建立,最早就是神学家们用语文学的方法来解读圣经,即不把圣经作为上帝的语言、上帝的福音来理解,而是把它作为某一个作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写下来的一个文本,对它做语文学的解读。所以,现在的哲学教授,他并不必须是一个哲学家,他更应该是一个哲学解释学家、是一个哲学语文学家、是一个哲学史家。以前常有人讨论到底我们是在做人文科学,还是人文学科,有人认为人文好像是不能够成为科学的。这是不对的。德语把人文科学叫做精神的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它就是科学。为什么是科学?因为它是一种语文学的研究,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后来,我们严格的把人文科学分成了文、史、哲和宗教研究、美学研究等,而在此之前,所有人文科学的总称就是语文学。这个应该说是语文学的第三个层面。
语文学的第四个层面。今天,语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按照西方人说法是forgotten origin of modern humanities,即是“现代人文科学被遗忘的源头”。大家早已忘了原来的人文科学全是语文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刚才讲的伯希和研究的这套学问,或者印藏佛学研究所做的这套学问,或者把做梵文研究的,甚至有时也把研究古汉语文本的那些学科当成是语文学研究。西方现在有一些大学里面有Department of classics,即古典学系,它们研究的都是一般大学的文史哲等系所不包括的学术。这些硕果仅存的冷门绝学的学术被人认为是语文学。这一方面它们的学术地位被弄的非常高,但另一方面,就像萨义德曾经说过的那样,在20世纪的大学人文学科里面,语文学是一个最不现代的,最不sexy的学科。大家都觉得语文学的门槛很高很难,但是它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义。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正好是从事这方面语文学研究的藏学家。
语文学的第五个层面,我认为语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学术态度。例如,尼采曾经总结了一个非常好的关于语文学的定义,他说什么是语文学?语文学就是“慢慢读的学问”,reading slowly。你必须要对一个文本专心致志,把一切的凡尘杂念统统抛弃,慢慢地、专心致志地去阅读和理解一个文本。你不能说我做一个学术研究,就马上要get it done,刚开始一项研究,就马上要想如何把这个文章写出来,马上要把这个研究成果搞出来。这是不行的,你必须仔仔细细地、反反复复地阅读文本,读书就像是一个金匠做一件金器一样,你像金匠一样对待一个文本,这就是语文学。语文学的态度还有很多很好的说法,例如傅斯年先生所说“史料即史学”,我们应该怎么做学问,怎么做语文学呢?傅先生说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就是语文学。再比如我的祖师爷、伯希和的弟子韩儒林先生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字空。”这句话后来被人误传是范文澜先生讲的,实际上不是,范文澜先生曾经自己指出是韩儒林先生最早讲的。他这是跟随伯希和先生学习和实践语文学的经验之谈,这就是语文学。对于每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来讲,我们都必须要有这种精神,你得仔仔细细去读一个文本,慢慢地去读一个文本,真正去理解一个文本。
到今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印度学教授Sheldon Pollock,他给语文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语文学是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是怎么把文本解释通的一门学问,是让文本产生意义的一门学问。对任何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甚至也包括社会科学,我们都必须要有这一套语文学的方法才能够做学问。为什么尼采会得出“语文学就是慢慢读”这么好的一个语文学的定义呢?因为他自己有过非常惨痛的教训。很荣幸,我跟尼采是校友,他也是波恩大学毕业的,我是波恩大学的博士,他没有上博士,他二十几岁本科毕业以后就去当了教授,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当古典语文学的教授。少年得志,这么年轻就当教授了,他写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书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叫《悲剧的诞生》,确切地说是《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这是他的第一本专著,他自己很得意,可没想到这本书一出来却恶评如潮,他有一个比他低两届的波恩大学的同学,名叫Wilamowitz-Moellendorff,写了长篇的书评,将一篇书评写成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未来语文学》。什么叫未来语文学呢?我最近才发现清华有所谓“未来学者”,实际上“未来”这个词在当时德国的语境下是一个贬义词,说你是“未来学者”就是说你你不是一个好学者,同样,“未来语文学”就是说你不是语文学,这最初是德国人讽刺歌剧大师瓦格纳的,说他所做的音乐是“未来音乐”,即是说你这个音乐我们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你在表达什么,也许未来有人会听懂你这个音乐,但现在肯定不是好的音乐。所以,尼采的这个学弟Moellendorff就借用这个说法,将尼采的著作称为“未来语文学”,就是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是语文学的著作。尼采这本书是研究古典悲剧的,可他没有引用过任何古典悲剧的原本,其中还没有一个注释(footnotes),全是引用瓦格纳的歌剧,所以说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语文学家,根本不配当语文学的教授。后来尼采疯掉了,从语文学教授位置上退上来。他对语文学刚开始充满了仇恨,到晚年他是又爱又恨(Hass und Liebe),又开始回过头来讲语文学,说语文学是慢慢读的学问,慢慢读的艺术,是像金匠一样的艺术。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语文学显然比在尼采那个时代更重要,我们现在做学问都要求你发很多文章,很快要出版专著。好在我们清华现在没这样的要求了,以前博士生都要求发表两篇C刊论文才能毕业,现在不要了。要求你发表很多著作的做法很不语文学,真正的语文学的研究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语文学的这个第五层面,即树立一种语文学的态度,对所有的人文学术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语文学的最后一个层面,也是我近几年来一直在讲的,这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为什么现在我觉得我对语文学的理解不是一种妥协,并不是不得不把伯希和的这套学术标准越来越降低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认为语文学可以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要学会living Philological,即语文学式地生活。很多人以为语文学是在学习和研究古典文本时才需要派上用场,事实不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看了《小兵张嘎》,你看到那段话用上语文学就会发现以前我们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今天你看报纸,你看今日头条,都应该要用语文学的态度,用语文学的方法去读。特别是现在,这非常重要。去年一年因为疫情,我被困在美国,每天经常看两个电视台的新闻,一个是CNN,一个是Fox News,看了近一年,惊讶地发现同一件事情在两个台的报道往往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新闻几乎没有现场的报道,或者说越来越少,基本上就像凤凰卫视刚出来的时候一样,窦文涛一个人可以讲上一天。现在的电视台就是几个人在那里轮流地讲,这样电视台或许比较便宜,不需要到现场采编。现在我发现这些新闻台基本上都是某个人在讲某件事,说的是同一件事,却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说法。如果你没有语文学家的修养,或者你仅仅看一个台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他们讲的完全不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所接受到的所有信息,你以为好像我们得到的都是即时的信息,事实上都是经过别人过滤了的。现在我们大多数人什么都不看,就看微信朋友圈,看今日头条,你觉得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实际上你知道的东西都是人家希望告诉你的,人家希望你接收的东西,都是很片面的。你看CNN,是左派的喉舌,除了在骂特朗普,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反正特朗普做任何事情都是坏的。Fox News正好相反,是右派。还有,前不久美国撤离阿富汗和塔利班这件事,我看中国的报道、美国的报道、中国民间的评论,以及我们官方电视台的评论,发现它们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今天没有一点语文学家的精神,或者没有一点语文学意识的话,那你肯定就只能接受一种说法,可能你每天觉得现在对这个世界非常了解,实际上你了解的都是非常片面的,是一个虚幻的,不是真实的世界。这让我对语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历史,傅斯年讲“史料即史学”,他认为只要把史料背后的语言、社会和历史背景了解清楚,历史就已经跃然在纸上了。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文本背后的社会的、历史的、语言的背景搞清楚,把它的context弄清楚,历史就在那里,不需要你多说了。后现代史学家也说史料即史学,但意义相反,他们认为不带观念的,不带某种意识形态影响的学术是不存在的,萨义德讲不受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污染的一个纯粹的representation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表述,没有纯粹的史料,它都是一种历史的叙事,历史的写作。这样的话,就像过若干年以后,比如说我们研究这代历史,那你看同时代人家对于这件事的记载,在不同的人笔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来研究它?我们应该相信谁?所以,要了解今天,了解现在当时当地的社会,就是在信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也绝对需要语文学,你才能够真正形成一个相对全面、多元或者正确的看法。不然的话,你会完全被某种带有偏见的叙事给带偏了。
今天语文学对于我们读懂文本的意义与当年伯希和所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刚才我讲到为什么伯希和能够读懂中国古典,想想再过一百年以后的人来研究今天的这些汉语文本,我想只懂汉语的人肯定更读不懂,里面出现了很多新的词汇,有的是民间新创的词汇,有的是变相的英语或者其他语言的词汇,各种各样的奇怪的词汇都已经到了今天这个汉语文本里面了,只懂汉语的人怎么能够都读懂呢?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人,语文学应该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态度,你一定要抱着一种很开明的,对各种东西都抱有接纳、接受、宽容的一种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去看待你所接收到的所有信息,这样才能形成相对比较全面的对世界、对人文或者对社会的看法。
从以上所说的六个层面来说,我们才知道语文学到底是什么。最后再总结一下,这也是尼采总结的,语文学是什么?语文学是一门让你能够理解过去、理解现在和理解你自己的学问。很多人说语文学今天不需要了,以前西方人说不需要语文学,因为研究西方现代小说的人说,我们都读得懂这些现当代的文学文本,为什么还需要语文学?不需要。除了读《尤利西斯》(Ulysses)比较困难,其他都能读懂。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的语文学困难,包括阅读当代的文本。我喜欢讲一个故事,我们研究西藏的,都知道1987年中国有一个作家叫马建发表了一篇小说叫《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个文本我以前就想去研究它为什么叫“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呢,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用后现代的想法来讲,这个标题非常有意思。“亮出你的舌苔”,显得西藏人很纯朴,很自然,空空荡荡emptiness,是空性,是大乘佛教教义的精髓。后来我发现,马建自己曾说过,这本来是两个题目,他希望编辑给他挑选一个,或者叫“亮出你的舌苔”,或者叫“空空荡荡”,没想到编辑觉得放在一起很好,就叫“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产生了很奇妙的效果。对这部小说要看我们怎么理解它?你要真正理解它需要很多的语文学的解读。就像今天我们阅读《人民日报》一样,如果你没有语文学意识,你根本看不懂今天的报纸跟昨天的有什么区别。当然,语文学对于理解过去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现在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看懂汉文古籍,我每年参加博士生面试,老师很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想研究古典文学,那么你读过哪些中国古典的经典文本?大部分人都没读过。我考藏学,藏族学生来参加考试,我问他们读过任何一本藏族的经典文本吗?没有!因为他们跟我们读书一样,这里选一段,那里选一段,唐诗选一首,宋词选一节,很多都是这样。这样的话,他们到底能够读懂多少的古典文本。所以,没有一点语文学的训练就读不懂这些古典文本,就失去了和古代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这么多圣贤作精神交流的机会,你根本读不懂它,或者你以为读懂了,实际上根本就读错了,或者你只读到它的某个部分,某一点。理解现在,为何也需要语文学呢?在今天,得到信息这么容易,这么方便,而且信息来源这么多元,有如此众多的,对同一件事情截然不同的描述、不同的看法和观点的时候,你怎么来理解它,你怎么界定自己的看法。我曾经多次在课堂上说过,我特别讨厌专家们给人家开书单,说你一定要去看这个书、看那个书。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特别是我觉得很多大学者们给人家推荐这些普通的很popular的书,似乎很掉价。我觉得一个专家学者读的书应该都是人家看不懂的、不想看的书。你何苦一定要去告诉人家你必须读这个书、读那个书,我说他们叫人读的书我一本都没读,我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我觉得更关键、更重要的是要教人怎么读书,没有一本书可以把你的世界观,三观全部改掉,可以改变你的世界。如果真有这样一本书,那是很可怕的,就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害了多少人,这种书是坏书。但如果你懂语文学的话,你会从字里行间理解它的意义,你肯定就不会盲目地受它的影响,所以,你应该先教人家怎么来看书。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解现实也需要语文学,理解你自己当然就更加需要语文学了。我们经常喜欢说佛教的“无明”观念,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因我们众生的无明而受到了障碍,我们不明事实的真相,可能更喜欢虚幻的东西,不敢直面自己,所以,必须以语文学的态度来认识自己。总之,不管你今天做任何的事情,如果你懂一点语文学的话,那你就能够更好的理解古代的圣贤,理解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理解你自己,和在你这个世界里面的位置。这是我一直在讲的语文学的初心。刚开始我确实以为,我在不断地做妥协,把语文学的水准不断的降低。到后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是希望语文学能够成为人们的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所有人文学者至少要接受一定基础的语文学训练,有很强烈的语文学意识。所有的读书人都应该有一种基础的语文学信念和意识,不然的话你读多少书都没用。 You are not what you read ,you are how you read,怎么读书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你读什么书,你只有和人家不一样地读一本书,或者只有读人家不读的书,或者读人家读不懂的书,你才会变成一个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人。这是我对语文学的理解。这些年来,确实我从一个专业的语文学家转化成了一名相对大众的语文学家。按照我原来的训练,我就是一个很狭隘的语文学家,就是做藏学,做藏文的古典文本,做佛教的文本研究。这些年来,特别是从2006年我从国外回来以后,我发现中国的整个学术一方面好像发展得非常快,快到让我自己也觉得没法想象。因为我们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这一辈人应该在学术上来讲是先天不足的一批人,从小没读过四书五经,也没读过外语,上了大学以后才开始补。所以我们的学术是先天不足的。但是我们这代人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上一代人比我们更不幸,等到文革过后开始做学问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很老了,而且他们跟西方接触很少,他们很快退出了学术舞台,我们这代人很快变成学术的中坚力量,所以很多人很快就当教授了,学术地位已经达到了我们老师辈一辈子达不到的高度,但是我们的学问真的那么好吗?我自己在国外待了16年,回来以后发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制造了那么多的学术垃圾,确实我们见到了太多真的是学术垃圾。为什么?因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如果没有语文学的基础就是不学术的。为什么刚才我说语文学是中国现代人文科学或者中国传统人文科学现代化的标志,这就是傅斯年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初衷,他就是想用西方的这套人文科学的学术方法,甚至用法国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这个汉学研究的方法,把它与传统汉学和儒学,与西域语文学(中亚语文学)这套学问结合起来,做成一套具有现代人文科学意义的学术传统,来改造中国的传统学术,打破了经学的权威,所以,这是中国现代人文科学形成的一个标志。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早已经忘记了,根本不知道语文学为何物了?我告诉大家傅斯年说的这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实际上是历史和语文学研究所,不是Linguistics,不是语言学,而是语文学,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人文科学研究所。到现在以历史学(和语文学)指代人文科学的的西方学术机构还有不少,例如我曾经做过访问学者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只有两个研究所,一个是自然科学研究所,一个就叫历史学研究所,历史学指的实际上就是整个人文科学,因为任何人文科学如果不是历史学的研究,不是语文学的研究,那它就是不科学的。但是,我们中国整个人文科学一方面好像非常活跃,成果很多,每年出很多书;但另外一方面,一直到前几年还是有博士论文整个没有一个注释的,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注释,我们不知道怎么做Index,这样的话,怎么可以避免生产学术垃圾呢?1990年代经常听从国内到海外去的学者说,海外学人都重视日本人的研究,为什么不重视我们中国学人的研究呢?西方人很多人还看不大懂日语,可能看汉语还更好,但日本人的学术著作非常的规范,严守这一套语文学的学术方法,言必有据,任何一个观点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都会给你一个语文学的交代,前人做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为什么要重新来做,我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而很多我们中国的学者,随便找个题目都觉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洋洋洒洒可以写上一大堆,他不知道这个题目可能人家早就研究过,或者你引用的文本根本就是一个不可靠的文本。傅斯年说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中国学者经常用汉代的文本说先秦,把宋代的文本当成是唐代的书,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对青年学者而言。如果你不接受一点语文学的训练,将来你自己怎么做学问?你的老师们在讲思想、讲理论,觉得很有意思,按照这个去做,老师或已经功成名就了,而你则不行。没有一个基础的语文学训练,你怎么可以做的下去。现在很多人面临这样的困境,当然这个东西在西方也一样,为什么西方人现在也说philology is the forgotten origin of modern humanities。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所有这一套东方的学问,以前不管是汉学、印度学,还是藏学、蒙古学,它们都是语文学的研究,后来全变成China studies,Tibetan studies ,或者Buddhism studies。所以,它们完全可以抛开任何的语言文本这样的研究,水准越来越下降。最近很火的一部美剧《英文系主任》(The Chair),就讲美国某一个常春藤大学的英文系的故事,这里面讲有很多研究古典文学的,讲中世纪文学的,讲莎士比亚的,讲乔叟的,没人愿意听了,学生们也不去了,老师讲的越来越没劲了。然后讲Sexy Novel的,这个课就爆满,课程都要设计得非常sexy。这一套的学术出现很多问题。有人天天爱讲理论,擅于理论的人讽刺我们这些语文学家,说你们每天打扮得整整齐齐,却没地方可去(All dressed up, but nowhere to go)。这些做理论的,特别是做后现代理论的,非常的吃香。但从198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大牌学者就倡导说要return to philology,发现只搞理论搞不下去了,德里达他们这些欧洲思想家在美国影响非常大,大家都言必称福柯,言必称哈贝马斯等等。然后研究文学的,研究英语文学的,做古典、经典的,不行了,没人来听了,甚至耶鲁的后现代学派都说没有什么真的是经典,经典全部可以打倒。此外,文学的经典里面无所不包,什么都有,你研究哲学也行、研究宗教也行、研究历史也行,这样文本不重要了,文学不重要了。所以,从1983年保罗·德曼(Paul de Man)开始,一直到2003年萨义德(Edward Said)为止,他们都是提倡要回归语文学(return to philology)。这些人都是搞理论的人,说如果再不回归语文学,我们这个学术就没法做了。当然很多人批判萨义德,说他们这些讲理论的人根本不懂这些文本,萨义德代表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但阿拉伯语他也不行。所以到最后他意识到这个理解文本很重要,要回归语文学,所以西方到后来各个学科都在号召要回归语文学。我自己受他们启发,我觉得我们在中国一定要宣传语文学,一定要倡导语文学,当然这在我们中国更加困难。西方人,特别是德国人,他们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过语文学。我在德国波恩大学时有一个同学,现在是德国马堡大学很有名的印度学家、语文学家,后来他很反感这个保罗·德曼、萨义德他们号召回归语文学,他说老子从来没离开过语文学,你叫我回到哪里去?以前你们批判我们德国的语文学家都是纳粹分子,制造了印欧语系、制造了雅利安人种,是纳粹的帮凶,现在又叫我们回归语文学,我要回归到哪里去?回到哪个语文学?他们从来都把语文学做得非常精致。而对于我们来说,尽管我们有过傅斯年这个传统,实际是语文学的传统。现在很多人在谈兰克史学,实际上兰克史学对中国的影响很小,傅斯年接受的更多是这套西方语文学的传统,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学术。大家看30年代、40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你看他们当年的水准,印出来的纸和印刷的条件之差,今天不可想象,但他们那个学术水准之高,可以说跟当时罗马东方学丛书没有什么差别,同样达到这个水准。可是到今天我们全已经忘掉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大学开《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这门课的动机,希望我们能够接受一点基本的语文学的训练,我并没有幻想让语文学再回到清华大学的人文科学的中心位置,取代文学、哲学、历史的研究,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是我想任何人文科学学者不管是研究语言的、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一定要接受最基本语文学的训练,一定要有基本的语文学的意识,有一点语文学的态度,甚至把语文学当作你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合格的人文科学学者,任何完全没有语文学基础的人文学术都是不学术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接下来请姚霜老师介绍这本书的情况。
姚 霜:非常感谢沈老师旁征博引,做了一个很宏观的关于语文学的诠释,其实里面囊括了很多沈老师近些年来不断更新的学术思考,因为这本书从开始想编是2016年,现在已经大概过了五年了。在五年的时间里,沈老师带领我们学生们一块做了很多关于语文学的讨论。沈老师讲的东西是非常的旁征博引,他在讲这段描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自己的学术经历。从我自己的学术经历上来说,我是做了藏学跟随沈老师学习后,才逐渐把我引入了语文学的大门。我原来是学艺术史的,在博士阶段,找到了一个关于藏传佛教寺庙的课题。那时候我在英国,在艺术史系里面去做这个课题,但遇到很多困难。做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其实对藏传佛教本身和藏族文化需要有很深的了解。而当时艺术史系没有办法给我这样的专业训练,我找到了沈老师咨询,他让我来到清华,相当于为我打开了藏学这个学科的大门。
打开这个门之后,我怎么去学习呢?首先,我先接受了基础藏文的学习。学完了之后,我找沈老师帮忙,想要他给我开一个有关西藏艺术、藏传佛教、特别是我要研究的教派的书单,或者哪些通史型的著作是必读的?他只是简单回答说:你现在就开始读文本吧。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阅读古典藏文(classical Tibetan)的有关藏传佛教的经典文本。在《何谓语文学》当中,有一篇文章是非常有名的佛教学家K.R.Norman写的《佛教和语文学》。它里面也提到,当时的西方人怎么了解东方文化。比如咨询教授关于学习佛教的入门书籍,应该以从什么样的方式去入门?Norman给出的建议是开始阅读经典,选一部经书,比如简单的就选《心经》。《心经》有很多的翻译本都拿来读,一字一句地去了解它,去了解它的名相,也就是“术语”,比如般若波罗蜜多的含义——也有一种说法是,语文学就是研究术语的学问。通过对每一个名相的学习其实就是所谓的入门的训练。我们其实在佛教研究当中,很多的学者编了非常多的词典工具书,读者可以通过一字一句的查询理解,从而在经典当中建立对于这一门知识的基础。这是从自己粗浅的学术经历为大家分享语文学实践的入门。
这本书可以说聚集了清华很多优秀本科生的极大智慧,他们现在很多已经是博士生了。他们在翻译、校对和编辑这本书,其实自己就是在进行一个语文学的实践。刚才沈老师说这本书的缘起是他当时2016年第一次开《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本科生课程的阅读材料。我特别记得的是,第一节课上大家期待沈老师讲一讲什么是语文学,但他在那堂课上让同学们直接开始阅读收录在我们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何谓语文学》的原文,然后让同学们现场轮流翻译。我当时是助教,结果第二节课一大半的人已经不来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发现语文学非常注重的一个训练就是翻译,是对文字反复的理解,很可能这样的理解是不断重复,不断的推倒再来的。
接下来,我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编辑思路。这本书我们一共有19篇的文章。开头的三篇文章为《何谓语文学》、《何谓语文学的力量》和《语文学在何处》。为什么要把这三篇文章先放在最前面呢?因为这三篇展示了1980年代末以北美文学研究所引领的一种有关“语文学”的学术浪潮。当时,一群哈佛学者商议,要举办一场关于语文学的会议。一开始很少有人响应,因为语文学在80年代理论泛行的北美文学中已经不sexy了。后来,会议召集人提到了保罗·德曼写过的一篇名为《何谓语文学》的文章,很多人就来兴趣了。所以在最前面的两篇,我们其实是从当代学术史的角度,为大家展现了为什么在当代去谈论语文学的这么一段历史。接着这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语文学的现状事实,即语文学作为现代人文学术的起源已经被遗忘了。所以本书的第三至第六篇文章是在展示语文学被遗忘的历史,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人文主义时期,语文学为何能被看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的原因。这里很大程度上是积淀于人文主义者的努力。所以我们在第二部分探讨被遗忘的历史中,从西方的学术史上为大家展现了语文学背后巨大的历史力量。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挑选了不同学科语文学实践的文章。比如汉学、梵语印度学、佛教研究领域等等。而在佛教领域,我们展示了两篇文章,一篇文章讲用语文学的方式去研究佛教研究,另一篇讲用理论的方式去研究佛教,其实给大家也有这样一个对比。这部分还囊括了一篇古兰经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我们理解现实的阿富汗和西方的那些似乎无法缝合的割裂,或许给予了一个经典文本历史的视角,很有意思;还有一篇则是以里尔克为例的诗歌研究。因此,我们列举了人文学术领域中不同学科语文学实践的案例,而这些学科如大家看到的,多数属于西方的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范畴,因为西方的东方学确实是将语文学的学术方式发挥到了极致的领域。
在各个学科介绍之后,我们来到了第四部分。第四部分为大家展现了两篇在西方文化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两篇文章:保罗·德曼的《回归语文学》和萨义德的《回归语文学》。这两篇之前都是有汉译本的,但我们又对它进行了重新翻译。还有哈芬和麦思林对语文学历史中埋下的种族主义的批判,他们为大家分析了为什么语文学,特别是在19世纪之后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帮凶。
最后第五部分为大家集中展示了当代语文学的理论发展。刚才沈老师在他的谈话中也提到了,如今在国际学术界里语文学最大的推手学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印度学教授Sheldon Pollock,我们收录了他的三篇非常具有学术高度的文章。Pollock最大的贡献是拓展了所谓传统语文学的定义,包括给语文学做了三个维度的划分,同时他提到了语文学与自由的关系,我认为这也是刚才沈老师一直在强调的语文学的精神,比如我们今天如何用语文学的生活方式去看待充斥在社会中的碎片信息。其实,如果我要建议大家读这本书的话,大家可以尝试反过来从后往前阅读,从最后一篇《语文学与自由》开始。可以先把对语文学的理解打开来,知道它不只关乎做学问,更加关乎的你如何去生活。
讲了编辑这本书的思路,接下来想为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作为一次集体的语文学实践背后的故事。由于疫情,很遗憾这本书出版以来没有举行新书发布会,也没有把我们的译者聚齐来分享这个成果。但是,这本书如果没有致力于语文学,愿意投身这件事的青年学子们,我们也没有办法使这本书成为今天的模样。五年前,我们首先拿到了这个原文,开始着手翻译。特别是在翻译过程当中,很容易发现那些看似读懂的内容,很有可能是没有读懂的。可以说,翻译是一个非常好的语文学训练,而我们的译文中也经历了整篇文章推翻重译的情况。而在2016年开课后,17、18、19年都有语文学的课程。我们将译文发给每一年课上的同学,去检验现有的翻译是否可靠,去进行反复的理解,去不断地重读文章。最后呈现的译稿其实可以看出我们当中很多同学们具备深厚的语文学功底了。比如在《未来语文学》这篇文章中,马洲洋博士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译注,包括对英语习语放置于在上下文中的翻译理解,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读懂文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其次,我们举行了长达快一年的校对工作。我们五、六个老师和同学组成了一个读书班,每一周花半天到一天时间,一段一段审看这些文章。我们的方式感觉特别像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道场:一人手执文本,一人念诵译文,两个人审看英文原文,还有两个人一旁听,大概是这样的模式。这本书里肯定还要很多不足之处,但通过校对的过程,最起码为大家排除了一些语文学的地雷。而挖出语文学的地雷(philological landmine)其实正是评论家,伯希和或者本书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扬•茨奥科夫斯基,最擅长的批评手段。他们善于审视文章和著作里的证据,特别是文本证据,引用的准确性等等。好的语文学家经常在书评中去挑“语文学的地雷”。因此,在校对过程中,这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头上。
其次,我们所拿到的原文本都是英文的,但里面涉及很多其他语种。比如《何谓梵文语文学?》里面有巴利文,一些德国的作者用了很多的德文,还有法文等等。碰到这些专业术语的时候,我们尽量集合自己团队和周边学者的力量,去尽量地翻译解决,保证我们这本书的质量。
校对完了之后还有编辑这一个步骤。其实编辑对于语文学实践来说是非常tricky(棘手的)。编辑有一些原则,常常注重的语句通顺程度,删除“多余的”的字眼,或者填补“缺少的”。而这样的做法其实如果放到语文学的学术当中,则是一个非语文学的做法。我们有很多杰出的佛教学者,比如说辛岛静志先生,在他们有关敦煌文献研究、佛经文本研究的著作里,展现了所面对的文本和自己的学术的诚实。比如对于这件残篇里文字的填补是十分谨慎的,而研究中没有弄明白的地方在注脚中会诚实地注明——没有就是没有,不懂就是不懂。他们不会为了某个论点,强行征引解读某一句话。一些人会认为日本的学术作品太语文学了,没有什么思想,但往往最后被后人频繁利用的也是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著作有时就像精致的字典,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
因此,我可能要跟各位译者表达抱歉的是,在最后的原文呈现上可能并不是大家当初交来的译稿。一些编辑修改也并不关乎主观,比如有时候是排版所限。在这一点编辑对语文学发展的影响,推荐大家读本书中《人文主义的语文学》这篇文章,里面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有很多人在这样去实践了。可以说,今天在我们这个出版行业蓬勃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对语文学非常友好的时代,因为印刷让抄本的错误(scribal errors)不会再次出现,不会是错误涌现的文本时代;然而,另一方面,出版又带来了一个坏处,即一旦有错误,那印刷错误则是成千上万倍的放大。在这一点上,沈老师提倡我们要用语文学的方式去阅读,因为我们要对所拿到的每一个文本保持一种批判式的自我意识。只有以这种批判式的自我意识,我们才可能越来越接近文本的真相。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我们编辑这个本书的一些语文学的实践。
沈卫荣:感谢好多跟我上这门课的学生,姚霜是其中一个。我们清华的学生做的翻译非常的好。我特别要提到两位同学,一位是王淼同学,我到现在没直接见过面,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语文学的三个维度》,第一次我请一位同学翻译了,我当时粗看了一遍译文觉得挺不错,但当仔细对着原文看译文时觉得好像每句话都有问题。去年疫情的时候,当时我在美国给同学们线上上课,其中有一位同学名王淼,我发现他每次对语文学课上的讨论有很多很好的看法,我就问他你能不能把这篇文章重新翻一下,结果他答应了,而且很快就翻好了,不仅翻译的非常好,而且还把原文中出现的问题也找出来了,说这段话的引文有问题,作者文中引马克思那段话的版本不对。我当时觉得这个王淼非常好,可惜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他,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国外读书去了,当年应该是我们世文班的三、四年级的学生。
另外有一篇翻得特别好的是萨义德的《回归语文学》,那篇文章我看英文读了很多遍,萨义德的文字很难懂,他是一个思想家、理论家,从语文学的角度去读他,经常不能很好的理解他的意义。当时已经有一个汉文翻译本,就是《文化与帝国主义》那本书里面的一章,但这个汉文翻译本根本看不懂。当时第一次上我这个课的学生中有一名中文系的学生,现在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叫屈晨钰,她重新翻译了,而且修改了很多遍。当这本书出版以后,我重新读了一遍萨义德的这篇文章,我觉得它翻译得这么好,让我对萨伊德的文字的理解比原来亲切、真实的多。这是很难达到的翻译水准!二位译者都是我们清华的本科学生,大家可以读一下我们书中的萨义德的《回归语文学》和谢尔顿・波洛克的《语文学的三个维度》这两篇文章,感受一下我们清华本科生的学术水准。
主持人:非常感谢沈卫荣教授和姚霜博士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语文学有了了解,语文学事实上是一门非常古老、经典的学问,但是在当代它又有些式微了,对我们很多人而言它是一个有些陌生的学科,现在我们对它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现场的观众包括线上的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提问1:沈老师您好,听了您的讲座之后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您。第一,关于全球史和语文学的研究方法的问题,我觉得全球史更注重的是对于弘大理论的建构,和语文学这种更强调文本和字句研究方法不同,我们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张力?还有,刚才您刚才在讲座中提到,语文学作为一门高精尖或高大上的学问,我觉得从当代公众史学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使这样一门学问满足普通公众对这样一种知识的期待,您有考虑写过类似于一些大家小书之类的著作吗?谢谢您!
沈卫荣:你是不是北大的,后来去德国待了一年,在北大上过我的语文学的课?
提问者:对。
沈卫荣: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实际上,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理论和语文学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下一门要开的课可能是要研究什么是理论。如你所说,语文学和理论常常被认为是互相对立的,前面提到顾彬教授觉得我写的那本书很好,一切都很好,但他要问我的心在哪里?因为他觉得语文学的著作里面是没有精神的,不给人启发,没有很多的思想。而理论相反,很多人会说人文科学没有理论指导就没有高度,没有意义。像伯希和这样的大师也常被人批判,因为他没有理论。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误解,其实语文学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某一种弘大叙事的建立的一个基础。刚才姚霜提到辛岛静志先生,他是日本当代最伟大的佛教语文学家,他做的什么工作呢?他编《妙法莲花经》的梵、藏、汉文词汇表,告诉读者经中出现的那些词汇原来梵文什么样,翻译成藏文什么样,汉文译文的不同版本又变成什么样。人家或不明白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干这个事情,这样的工作看起来这么机械。没想到佛教研究的很多突破都从他那里开始的,比如他写了一篇关于净土的文章,他说中国佛教净土宗最厉害了,可他的研究发现净土信仰的形成或源自中国人犯的一个翻译的错误,这个翻译的错误甚至可能是故意犯的,因为净土,pure land,这个词本身不是一个形容词和名词的结构,不是指纯净的土地,实际上本来是一个动词和名词的结合,净土的净是动词净治的意思,即是要通过你的菩萨行来净治、庄严这片土地。它原来是这个意思。你看整个中国的净土信仰,经过语文学的研究,一下子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所以,辛岛静志曾说我不只是在做语言的研究,我是一个佛教思想家,哲学史家,我是希望来通过语文学的研究来弄清楚佛教本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做语文学学问的目的是要解读佛经,解读佛教思想的,并不是只是在做一个技术活,他只是想把佛的思想在原来的语境中,原来的宗教、语言、社会语境中来解读它。相反的例子是,我们知道的伟大思想家,研究圣经的斯宾诺莎,他是一位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他写过一本书叫《神学与政治》,波洛克说他这个书实际上不应该叫《神学与政体》,应该叫《语文学与政体》,为什么?就是因为斯宾诺莎通过对圣经的语文学的阅读,把圣经当做一个文本,他用语文学来细致地分析这一个文本,搞清楚这个约翰福音或者马太福音是哪一个作家在哪个时间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这段东西。最终他整个地解构掉了上帝,解构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所以这是一个语文学的成就。他说好的阅读最后能达成一种好的政体,能打破经学、神学的权威,建立好的民主政体。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利用的是语文学的做法。现在我们大家津津乐道的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很多人把它误解成是陈寅恪的政治态度,显然不是,这就是语文学家的精神,独立的意志、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这就是语文学,所以语文学并不是没有思想的。
另外,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到底理论和语文学是一个什么关系?刚才说理论家们批判语文学家说,你们All dressed up,却 nowhere to go,你学那么多干什么呢?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语文学家开始嘲讽理论家,说你们有lots of date,却nothing to wear,就是你经常有很多约会,很热闹,可是你没东西可穿,一天到晚在那里夸夸其谈。这里也说一个语文学的典故。刚开始我们这位在哈佛念书的马洲洋博士,看来他没有跟美国人date过,不知道这个date是什么意思,他觉得Lots of date是说有很多日期,没有衣服穿。后来我说小马哥,你怎么连这个也不知道呢?美国人的date很难翻译,跟中文谈恋爱不一样,到底这个date我也没搞明白,我也没date过。这个是批判理论家的,说他们生活很热闹,有很多关系,但是你们没有真东西可拿出来武装你。我想理论给人一种启发,给人一种perspectives,一种approach,但它不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确实理论可以指导你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是某个理论直接指导你如何做研究、如何读文本。萨义德的这个东方主义思想,显然是在他读了无数西方人对东方的representation以后才得出来这个东方主义的理论。具体到全球史和地方史,刚才我说的这一套语文学的研究,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日本京都大学的杉山正明教授,他本来是一位优秀的语文学家,他的role model就是伯希和,学了很多语言,当时要把波斯语的《史集》那份资料解读出来,用它来研究蒙元史,他原本做得很好。但是,最后这类语文学研究文章他写的很少,他最初成名是因为他的语文学,后来他就开始写大元史,把整个蒙古史作为一个global History,作为一个全球史的标志,就是蒙古人打破了东方和西方的界限,现代世界是从蒙古时代开始形成的,蒙古对世界的征服开始形成了现在的globalized world,没有东方和西方了。这是他的一个理论的建构,这个理论建构无疑是成功的,但作一位为蒙元史学家,他的权威就倒了。他提出了新的一套蒙元史叙事,但缺乏语文学的权威性。但是在他的影响下有一大批做这种类型的global history,这些人完全没有语文学的训练,他们的著作则更加等而下之了。我以前在《大元史与新清史》那本书里举过一个例子,有个美国人叫Jack Weatherford,写了一本书叫《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这个人我跟他在美国一个学校里同事过一段时间,叫玛卡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专门写畅销书的,前一本书叫做《货币史》(The history of money)。
那时候我在那个学院代课,他有一天请我吃饭,还有一个蒙古学者,叫纳日碧力戈。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写一本关于成吉思汗的书,我问他懂蒙古语文吗?他说当然不懂。以前学过蒙古史吗?没有。我说那你怎么写?他说五年以后,我把这个书肯定写出来。以后每年他去外蒙古,骑着马上去考古,体会当时成吉思汗是怎么样征服世界的。大概四年不到这本书就出版了,我在飞机场的书店里看到,莫名惊诧。它又是一部全球畅销书,很快就翻译成汉语了。全球史当然有意思的,但是读他这本书,则觉得它完全是一个Post-modern creation,是后现代的对成吉思汉的想象,他把成吉思汗写成一个非暴力的、宽容的,对各种宗教都抱着欣赏的后现代的世界君主。我多次想好好读这本书,但我没有办法读完,我读了前言和结语就觉得这是一本烂书。可是它在全球畅销,后来他又连续写了三本书,都是关于蒙古历史的,都很畅销。我想全球史不是应该这样写的,你至少得懂一点语文学吧。刚才姚霜也说了语文学家要抓别人家的错那是一抓一个准,哈佛的那位教授批判两个美国鼎鼎大名的比较文学家、语文学家,一个叫Seth Lehrer,还有一个叫Hans Ulrich Gumbrecht,前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的文学院的院长,后者是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的讲座教授,他给他们的学术研究起了一个名字叫超语文学(Metaphilology),说它根本不是语文学,是未来语文学,里面的错误太多了,对文本的解释根本就是不通的,我想从中也可以看出理论和语文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姚 霜:这个也是非常困扰我的问题。一方面虽然跟随沈老师学习,挑灯夜读好像在做一件特别不性感的学问。另一方面,当你面对这个世界,不可能不去想更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我也经常质问自己的学问怎样可以更具有关联性,特别是你所讲的,对于公众产生意义?
首先大家认为语文学很难产生关联,或者把语文学和理论二元对立起来,是很大的偏见。所谓的关联其实来自于我们的理解,而我们只有通过语文学对文本更好地理解,才能打开关联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通过文本阅读,能让我们看到更多了解文明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才使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关联。当然,我非常同意去了解宏观的叙事,当有一个全盘的思想,有可能阅读文本的时,对文本阐释的深度和维度也许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辅助的,而非对立的过程。
另外刚才您建议沈老师多写一些“大家小书”,宣扬何为语文学。首先,我们这本书其实有点以语文学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语文学。另外,与其去告诉大家什么是语文学,不如让大家开始语文学的实践。大家都可以拿到自己手边的文本,开始阅读语文学式的文本,可以就从阅读新闻开始。这或许也是一种公众语文学的实践。在我们的文章当中,提到过葛兰西在狱中曾经教工人们去阅读,有一段“工人语文学”的浪潮。与其说推出“大家小书”,还不如倡导大家热爱语文,以语文学的方式去阅读、理解。
沈卫荣:茨奥科夫斯基曾写了一本《超语文学》,用的词是metaphilology,最后说我们应该不忘初心,回归到对文本、对语言的热爱,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人文学者。
提问2:你好沈老师,我想问一下在日常阅读中有没有好的方式、方法可以训练我们自己能够更加轻松、有趣的方式?第二,我发现在网上营造的信息茧房中,有时候阅读就会停不下来,怎么从语文学的角度对自我优化,跳脱出来?
沈卫荣:谢谢你的提问!实际上,刚才已经说了,读书一定要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你慢慢地读,去理解这个文本到底想说什么。前面已经说过,我从来不给普通读者推荐要看什么书,我也不认为中国人读书一定比外国人少,我也不觉得看微信朋友圈就是不对的,微信上有很多好的文章。很多人说,德国人特别喜欢读书,我说我知道德国人每天早上一块钱买一张图片报,第一页都是一个裸体的女人,都是标题,没有什么真正有营养的东西。不见得德国人就比中国人读书多。
我也在日本待过三年,日本人读书,站在便利店里半天不走,大部分时间都在读漫画,不见得比我们读书多,读更好的书。我们读微信朋友圈并不一定就表明我们不读书或者不看纸书,或者不进图书馆了。问题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语文学的意识,不光做学问,就是读一般的媒体也是如此,你现在看我们大家基本都是标题党,因为我们的阅读注意力的时间越来越短,标题党一下给你定了调子,你不注重细节很快就被它们左右了。
最近我很惊讶的就是阿富汗这个事情,我一看CNN讲的跟Fox News讲的完全是两个事件。再看我们中国的微信朋友圈里讲的和中央电视台的又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能被某一种观点左右,一定还是要关注这个事件后面的细节,要有你自己的批判精神,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思想,或者批判精神,要用到这个上面去阅读。当然,很难保证一个人能够脱离现实的政治、权力、利益对你的影响,但要尽量减少这个东西。做学问更是这样,一定要慢慢的读,真正把这个读懂。我自己是学藏文的,天天读藏文的文本,有两个体会,一个是,我可能比很多藏族的人读藏文的古典或者宗教文本读得比他们更懂,理解也深刻,但也有可能一个西藏人讲了一个如此简单的东西,我却可能就理解错了,根本就没读懂。因为我一直在关心那些很复杂的东西,因为我不是native,如果我是一个汉学家去做汉语的文本,我现在也经常发现我到文章三校才发现原来的断句断错了,完全不同的意思,经常会是这样的。我曾经看过当时在美国的一位德裔著名汉学家,他去美国当汉学家,听说还差点当上了哈佛的汉学教授。他翻译了玄奘法师传。文中那些我当时不太懂的东西他全翻译对了,而很多读起来简单的东西他却全部翻译错了。里面的佛教词汇,特别是其中出现的梵文词汇,他都找出来原文是什么。而那些比较简单的,我现在还记得文中说玄奘“性好简文”,实际上简是指书简,文是文字,他说玄奘从小就喜欢简单和文化,他居然是这样理解的。语文学在当代汉学里面的应用很差。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点意识的话,你以为你读懂了,实际上经常是读错的。还有,我在德国的时候上过一门汉语解经学的课,读《论语》,“即来之,则安之”,老外都读错了。实际上,我们也经常读错,我们从小就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既然来了,你就在这好好的安定下来。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意思,“即来之,则安之”是使动用法,既然你把人家招来了,则一定要让人家在这里安居乐业。这是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从小就读错了。当然很多字自小读错的例子就更多了。我一直担心我对某个字读不准音,我上课为什么不点名,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的名字我都不认识,点名点错了怕人家笑话。北大的林建华校长说燕雀安知鸿鹄(hao)之志,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丑闻,后来我说我们小学老师教我们就是燕雀安知鸿鹄(hao)之志,没说读鸿鹄(hu)之志,我从来都读错的。这类错误有些不严重,但有些是很严重的,所以没有语文学,你以为你理解了的东西,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解。
提问3: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语文学、语言学、中国传统的小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我有朋友研究古代汉语语法,他经常讲他自己研究的和中国传统的小学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今天听您在讲语文学,好像语文学可以包括语文学这种语言学这种语法研究和小学研究。我想问一下,语文学的独特性在哪里?谢谢!
沈卫荣: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语文学在中国不流行,大家接受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语文学这个名称本身的翻译问题,我现在说语文学是love of the word and text,是对语言、文本的热爱,故译语文学没问题。但是很多人翻成小学,或者翻译成朴学。以前钱文忠翻译的本杰明·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他把哲学翻成理学,语文学翻译成朴学,这里面就有问题,确实语文学的很多方法跟我们的小学,特别是训诂和文本对勘是很一致的,但我们今天讲的语文学是西方的一门学术。中国传统的小学与西方语文学的诸多分支(branch),有很多是相应的,但并不完全一致,语文学可以涵盖这些东西,它们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语文学这个词的翻译,最早傅斯年就搞不定,他一会儿翻译成“语学”,一会儿翻成“言语学”,胡适就把它翻译成“古文字学”,他为北大奠定人文学科的科目的时候,就列“古文字学”(后面是括号philology),陈寅恪也把它翻译成“古文字学”,他说我在德国学古代东方文字学,他是把它看成文字学的,他也不完全认同它是小学。实际上,在语文学里面很多就包括伯希和他们那套学问,它们可能跟中国的小学接近,但不完全一样。前面提到过,伯希和有一种中国传统学者不具备的能力,即解读在汉语文献中出现的非汉语词汇,他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对这些词汇做审音勘同,他知道这个字、词的原型是什么,来自哪种文字,他能判定这个词汇原来是一个匈奴语,或者是突厥语里面的,或者是藏语里面等等。这些东西正是中国学者所不能的,中国学者很少人能读懂《汉书》的“四夷传”,因为那里面都是些外来的词汇。中国人对古汉语文献中的外来词汇,习惯于尝试用今天汉语中这个字、词的发音来解读它们的来历,常常都是错的。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Russia翻译成俄罗斯呢,懂语言学的就知道,中国人没法直接发R这个音,必须把后面的元音提前,然后才能发出来Urussia,即俄罗斯这样的音。中国已故的一位蒙古学大家,他的名字叫林沉,或者叫亦邻真,这两个名字都来源于藏文的Rin chen,是同样的意思,同样也是因为没法直接发r的音,非要把原音前置,成为Irin chen,所以成了“亦邻真”。这些东西中国小学家们不懂,西方语文学者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中国的小学或者朴学,包括钱大昕的乾嘉学派,常常被西方人翻译成Chinese philology,即中国语文学,这并不完全恰当。它们的方法或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实证的研究,但是你想这个乾嘉学派的大部分人做的都还是经学研究,它们是为解经服务的,和现代语文学,一门以打破经学和神学权威为目的学问,在本质上也是有区别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笼统地讲语文学的话,确实我们也有这个传统,很多内容是一样的,包括西方人讲的lower criticism,higher criticism,这些文本的对勘和考据,对作者的考订和成书背景和过程的考察等,中国小学里也都有,但它们也是有一些差别的。
姚 霜:我也回应一下这个同学所讲的,你刚才问了非常好的理解语文学的问题,为什么?就是涉及翻译。刚才前一位同学也问怎么样在生活中实践?我认为最好的实践语文学的方式就是翻译。
沈卫荣:有人说中国人现在学历史的也好,文学的也好,经常说这些古典文本要不要翻译成现代汉语?通过翻译现代汉语,可能就能真正的理解这些文本,有时候我们引用一段文本,但不一定真的理解,但如果要翻译成现代汉语或者外语,你就必须更好地理解它。你说的翻译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一定要翻译成外文。
姚 霜:是的,翻译作为非常好的实践语文学的方式并不局限于多语种之间。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何谓语文学》整本书里面不同方式的语文学实践。语文学,并不是一个单数。《人文主义的语文学》这篇文章的标题,语文学就用了复数(philologies)。这篇文章里介绍了在近代欧洲人文主义者们展开的不同的语文学实践。因此,我们今天理解的语文学实践也可以是一个复数。但是如果要总体谈论语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它又可以是一个单数——一种不断地去理解,不断地去自我批判的精神。
沈卫荣:而且我们对语文学的阅读和新批评主义的close reading要做区分,以前有一个误解,包括保罗德曼故意误导,认为close reading就是语文学的阅读,因为我们把close reading翻译成精读、文本细读,实际上正好是相反的东西。Close reading可能跟尼采说的有点相近,慢慢的读,但本质上它是反语文学。语文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如果你今天对这个文本只能理解到这里,你对背后的背景、语言不了解,哪一天有新的文本、新的资料发现,就会加深和改变你原来的阅读,会出现不断的改变,语文学就是一门不断犯错误,不断改正错误的学问,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究竟。Close reading从本质上来讲是另外一种阅读方式,close reading是让你切断文本和它原有的作者以及它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所有联系,要求读者就看这个文本,来研究这个文本的结构,文本的词汇选择等,你不要拿你自己所有的任何的人文知识去填充,你就慢慢地读、仔仔细细地读,终于有一天你会豁然开朗,突然明白了文本所要传达的意思,close reading应该是指关起门来阅读,而不是我们说的语文学式的细读和精读。
主持人:我知道还有一些现场的观众有问题,但我们的直播还是有比较精确的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交流。今天沈卫荣教授和姚霜博士给我们精彩分享了何谓语文学,在听这个报告的时候,我特别回想起我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时的一位哲学教授关子尹先生,他是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的博士,翻译过卡西尔的《人文科学的逻辑》。他对哈贝马斯是很推崇的,但是他提到德国很多学者的“学力”,跟今天沈老师所讲的语文学其实有着很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我特别感动的是,在沈老师与关先生的身上都看到了对文本的敬畏感和做学问的庄严感。再次感谢沈卫荣教授和姚霜博士的精彩报告,谢谢大家!
——全文完